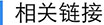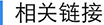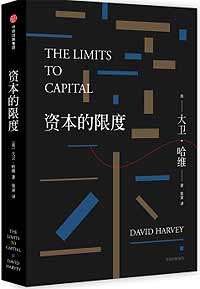 在20 世纪70 年代的混乱中胜出的解决方案(尽管各处的胜负是非常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或所谓“自由市场”的路线,其中带头的是金融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美元的问题)。这次胜利绝不是无可避免的,也不是没有它自身内在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矛盾和不稳定性——后一点如今已经极为明显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个实在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在《资本论》第1 卷,马克思证明了一个社会越是符合去除国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权力的不对称——有的人拥有生产资料,有的人则被排除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之外——就越会造成“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 卷,第645 页)1。30 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可以构造一种可信的论证——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Neoliberalism)2 中试图说明这一点——资本家阶级的主导派系之所以会提出新自由化的日程,从最开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从20 世纪70 年代的乱局中兴起的资本家阶级精英分子恢复、巩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构了他们在全世界的权力。
在20 世纪70 年代的混乱中胜出的解决方案(尽管各处的胜负是非常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或所谓“自由市场”的路线,其中带头的是金融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美元的问题)。这次胜利绝不是无可避免的,也不是没有它自身内在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矛盾和不稳定性——后一点如今已经极为明显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个实在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在《资本论》第1 卷,马克思证明了一个社会越是符合去除国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权力的不对称——有的人拥有生产资料,有的人则被排除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之外——就越会造成“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 卷,第645 页)1。30 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可以构造一种可信的论证——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Neoliberalism)2 中试图说明这一点——资本家阶级的主导派系之所以会提出新自由化的日程,从最开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从20 世纪70 年代的乱局中兴起的资本家阶级精英分子恢复、巩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构了他们在全世界的权力。
这次政治转变——阶级权力的恢复和重构——意义重大,需要更加详细地予以评论。阶级权力本身是含糊的,因为它是一种难以直接衡量的社会关系。但它的行使需要一个看得见的必要条件(尽管绝不是充分条件),即收入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这些积累和积聚的存在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都得到了联合国报告的广泛关注。当时人们发现,世界上最富有的358 个人的资产净值“等于世界上最贫困的45% 的人口——共计23 亿人——的收入总和”。世界上最富有的200 个人“在到1998 年为止的四年间使他们的资产净值翻了一倍有余,超过了1 万亿美元”,因而“世界的前三名亿万富豪的资产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及其6 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些趋势一直在加速,尽管各处的加速并不平均。在美国,前1%的收入赚取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 年到2000 年翻了一倍有余,而前0.1% 的人达到了原来的三倍有余。从1972年到2001 年,“从低往高第99 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87%”,而“第99.9 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497%”。在1985 年的美国,《福布斯》400 富豪的财富总和在按照通货膨胀予以调整之后“为2380 亿美元”,“平均资产净值为6 亿美元”。到了2005 年,他们的平均资产净值则是28 亿美元,全部资产达到了1.13 万亿美元——“超过了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转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管薪酬的急速上升。“按照今天的美元来计算,普通的首席执行官在1980 年可以挣160 万美元年薪”,但到了2004 年,年薪数字上升到了760 万美元。布什(Bush)当局的税收政策令人愤慨地使这些差别更加悬殊了。税收减免的大多数好处都流向了前1% 的收入赚取者,而且最近的税务法案只为“处于收入分配中段的人”削减了大约“20 美元”的税负,而“前1% 的人当中的前十分之一尽管有530 万美元的平均收入,却平均可以省下82415 美元”。这些趋势并不局限于美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掌权了——这些政策在地理上的扩散是非常不平均的——收入和财富极其悬殊的差距就会随之出现。在1988 年之后的墨西哥,随着私有化和经济结构转换的浪潮,有24 名墨西哥亿万富豪出现在了1994 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排在第24 位。在2005 年,严重贫困的墨西哥拥有了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亿万富豪。在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实行市场改革的几年间,七名寡头控制了近一半的经济。随着市场改革,东欧和中欧也同样显示出了不平等程度的剧增。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前1% 的收入赚取者到2000 年为止已经把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一倍。东亚和东南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最初还能够把强劲的增长与合理的分配平等结合起来(如韩国),但自1990 年以来——主要是在它们的经济遭受了1997—1998 年猛烈的金融冲击之后——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却出现了45% 的增加。在印度尼西亚,少数贸易巨头的大笔财富避开了这场创伤的侵害,却有大约1500 万印尼人失业。
(文章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资本的限度》,作者:[英] 大卫·哈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