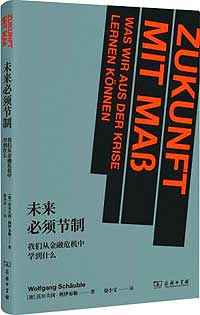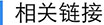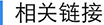|
|
| 作者:(德)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出版:商务印书馆 |
贪婪将平衡的发展趋势打破
在朔伊布勒看来,从国民经济学角度出发对这场危机的诸多解释,如美联储长期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房地产市场掉以轻心的过热(受社会与融合政策的驱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取消证券商债务上限的灾难性决定;再融资以及遍及全球的超大规模抵押;还有证券化加上一直将手伸进德国居民存单里的所谓创新所造成的信贷风险等等,乍听起来颇为可信,且有理,但都过于浅薄。他认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危机是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人由利己的状态升级到了贪婪造成的。不错,利己是自由市场发展的驱动力,但贪婪将平衡的发展趋势打破。“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危险的无度行为,正是这样的行为导致了这场危机,进而从总体上威胁到我们的自由经济体制。他的分析逻辑是,人类历史上不可能存在无穷尽、不间断的直线上升式发展。在成功与进步之后,倒退随即而来。这丝毫都不能说明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失灵。否则,过去的数十年何以会运转良好并创造出繁荣?问题还是在于人的本性。
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德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曾敦促过适度与节制,为此遭到了一番嘲笑,因为人们不愿意相信苦日子会重新再来。上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石油危机才让许多人幡然醒悟。而这样的悲剧,在2008年再度上演。不仅如此,朔伊布勒还觉察到:这很可能是信息时代的第一次金融大危机,人们错误地以为金融信息和金融产品可无极限地衍生和发展,以为复杂到无人能理解的金融衍生品,就能掩盖其相比抵押贷款式的传统金融方式的虚弱。“利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我们有着很好的理由,可以将之塑造成一种经济制度抑或社会制度的基石。人们只要能够因其行为获取相应的成果,他们的工作效率就会倍增,同时内心的满足感也会更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利己一旦过度,便是贪婪,这就十分危险:贪欲会损害乃至摧毁一个合理的制度。”从挖掘人性的贪欲与无度入手,进而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呼吁节制与适度,应该说,朔伊布勒抓住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成因。
社会市场经济核心原则是秩序政策
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地克服重重困难和此起彼伏的危机,其“并不完美,但是良好”,因而在经受了形形色色的责难和质疑的过程中,仍保持着相对的连续性。继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奇迹”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德国经济逆势而上,“德国制造”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追溯既往,朔伊布勒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是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秩序自由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频发,古典自由主义逐渐丧失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调节功能。一些新的经济理论开始出现,其中之一是凯恩斯主义。而在德国,随着“一战”的失败、魏玛共和国的持续动荡以及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酝酿,并在上世纪30年代期间形成新的学派。因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朔伊布勒在书中提到的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等,当时都在德国西南部的弗莱堡大学任教,世人因此称之为“弗莱堡学派”。该学派的理论要点是在古典自由主义与中央计划经济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主张“国家必须在资本家面前保护资本主义”。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些人遭到迫害,有的流亡国外,但他们并未终止探索和研究。“二战”结束以后,同弗莱堡学派联系密切并深受其影响的路德维希·艾哈德成为英美双占区负责经济事务的最高决策人物。艾哈德在1948年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基本上采纳了“秩序自由主义”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如果说“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的飞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核心因素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确保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在极短时间里实现了德国的重新统一。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与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亦即市场经济运行与社会政策制度化两者间的互补性是其制度设计的着力点,也是德国经济成功表现的关键所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家们普遍重视伦理道德与价值导向,并将之视为经济秩序的前提条件。朔伊布勒始终强调这一核心精神和理念。
“将责任与自由绑定”
如何走出这场危机,未来究竟要做出什么改变,当然没有现成的药方。但朔伊布勒坚信,要走出危机,“制度的出发点必须是人的本性,而并非人的理性”,必须“将责任与自由绑定”、“在自由与调控之间做到正确的平衡”。为此,他着重论述了以下六点:
第一,朔伊布勒援引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观点: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可自我充分调节并再生的制度,还是要依靠国家的调控。德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的政策并不是去救大银行,而是建立一揽子计划来提供流动性、提供信贷,从而保障金融基础,目的就是建立共同信任。
第二,重新建立盈利与亏损、风险与责任相互挂钩的措施。例如限制银行向第三方转嫁风险等。德国联邦政府整顿银行的模式,是毫不含糊地削减资产负债作为复苏的前提条件。
第三,朔伊布勒对评级机构缺乏透明度和没有真正建立起可信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泡沫总是在威胁到制度层面时才会破裂,公开透明毕竟是自我保护的唯一办法”;“从金融业的关联范围以及当前的危机来看,如果国家试图通过监管与校正性动作来解决问题,而市场参与者自身却不行动的话,其效果并不必然更好”。
第四,为了增加透明度并遏制风险,不仅需要制定更好的规章制度,也要分散风险。人必然会犯错,既然如此,分散决策就会好一些。这样一来,市场参与者便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
第五,与单一性经济相比较,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能较好地防止系统性危机和沉重的损失。由此,朔伊布勒坚持认为,德国在有大型企业集团与大型银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继续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与社会伙伴及客户之间直接接触的,企业管理是家庭传统式的,这些都紧密与社会价值观相连,这些中小企业与个体的之间的责任是最直接的。
第六,培育防止无度的意识和加强“全球化的教益”。“我们难以改变人的天性,例如贪婪与吝啬。但是,我们可以正面宣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负责任的行为不会让我们错过或失去什么,而只会赢得休戚相关与集体精神”。
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朔伊布勒认为还需坚持贯彻两项基本原则:处理自由原则时的辅从性以及在处理那些没有国家救助便无法稳定的企业时坚持结果与资本挂钩的原则。所谓“辅从性原则”即:首先,由银行与投资人承担责任。供给方按规矩行事,其中包括对风险采取比较有效的预防措施。需求方必须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对项目的风险要有确切的了解。当一个项目或一项交易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人的理解力时,也许就该将之放弃。其次,维护充分适度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刺激体系,是造成风险的人必须承担责任。
“钟摆有时会向一个方向过度地摆动,接着又会朝着另一个方向过度摆动。关键在于适度”。朔伊布勒称,此次经济危机让我们找到了一种“适度与责任的新文化”。在欧美社会,出于赢得选票的需要,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已甚少触及重大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而对一些能博得眼球的日常琐事津津乐道。对此,朔伊布勒提醒人们关注道德与精神重建,不然的话,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贪欲与无度的颓势。
要避免市场经济的无度与贪欲,需要政治秩序架构和社会价值取向,这应该就是朔伊布勒从此次金融危机中汲取的宝贵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