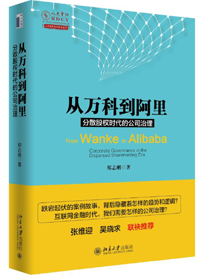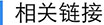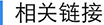|
|
|
作者:郑志刚 |
2015年7月发生的宝能“举牌”万科从开始就注定了不是一场单纯的并购(参见本书“‘险资举牌’是单纯的并购吗?”)。由于并购对象万科的管理层是以王石为首的创业团队,使万科股权之争很快陷入是应该遵循资本市场“股权至上”的逻辑,还是应该对创业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投资予以充分激励的争论之中。
正当围绕万科开展的实务和理论之争如火如荼时,哈佛大学哈特教授获得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传来。哈特教授发展的不完全合约理论告诉我们,虽然面临由于合约不完全导致的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但投资者依然愿意把自有财富交给陌生的经理人打理,是由于公司向股东做出未来可享有所有者权益的承诺。对于合约中未规定事项,股东拥有剩余控制权,表现为对公司资产重组等事项以投票表决方式进行最后裁决(参见本书“哈特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与‘现代股份公司之谜’”)。更加重要的是,哈特教授告诉我们,控制权安排的实质是向股东提供投资的激励(参见本书“对哈特不完全合约理论的几个误解”)。因此,在控制权安排模式选择上我们需要围绕上述实质展开。
分散股权时代的公司治理如果说哈特教授发展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为我们解决分散股权时代的公司治理模式选择问题提供了思考方向,那么发生在身边的阿里的故事则为我们近距离观察如何防范“野蛮人入侵”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参见本书“阿里上市启示录”)。借助合伙人制度,阿里事实上变相推出了不平等投票权。持股31.8%的阿里第一控股股东软银和持股15.3%的第二控股股东雅虎竟然放弃在普通人看来至关重要的控制权,而同意持股13%的马云合伙人对阿里的实际控制。而软银之所以同意放弃控制,原因在于,变相推出的不平等投票权事实上完成了创业团队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从短期雇佣合约到长期合伙合约的转化,实现了交易成本的节省(参见本书“从万科到阿里:公司控制权安排的新革命”)。这事实上同样是Facebook、Google等美国企业和百度、京东等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选择发行双层股权结构股票背后的玄机。
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无疑将加快上述控制权安排模式创新的进程。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身份的重叠使得资本的责任能力弱化许多,以往相对稀缺的资本退化为普通的生产资料。而随着投资者进入门槛的进一步降低,任何需要资金支持的项目都可以借助互联网金融轻松实现外部融资,而不再受到资本预算瓶颈的限制。业务模式竞争背后更多反映的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劳动(创新的业务模式)雇佣资本(通过互联网实现外部融资)”的时代悄然来临(参见本书“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公司治理”)。
随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在被加速的控制权安排模式创新进程中,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把握控制权安排的实质内涵,努力避免对控制权安排的误解和滥用。在杭绍台高铁项目中,有人担心民资成为控股股东会制定垄断高价,损害当地居民的福利(参见本书“民资成为控股股东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我们看到,股东通过投票表决对重大事项的影响力应该限于不完全合约中尚未涉及的资产重组和经营战略调整等事项,而对于合约中明确规定的提供客运服务的责任和义务则不应该成为股东讨论和决定的范畴,而是需要严格履行合约义务。因此,即使民资成为控股股东,也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为所欲为。一些人对杭绍台高铁项目民资控股的担心显然是对控制权安排实质内涵的误解。
除了对控制权安排实质内涵存在误解,现实经济生活中还存在滥用控制权安排的例子,以及认为控制权安排可以代替政府监管作为的观点。一些学者主张,从央企整合开始,推动中国石化、电力、煤炭企业间的链式整合,全面升级建立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能源系统,实现中国能源消费由一次能源向二次清洁能源的转化,“以小代价换时间、以小博弈换蓝天”。我们看到,上述建议仅仅是用产权控制来代替政府监管作为,并不能实现预期的治霾目的(参见本书“国企整合难治霾”)。这显然是控制权安排的滥用,因为控制权的安排只有在涉及投资激励时才变得重要。无论用控制权安排来避免垄断定价,还是用控制权安排代替政府监管作为,其实都是对控制权安排实质内涵的误解。
从2003年到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共发生了2 558起实际控制人变更。其中实际控制人从国有性质转为非国有性质共628家,占到全部变更的25%。上述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的改变既是重要的,也是不重要的。其重要程度依赖于一个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给定一个公司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第一大股东性质的改变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变得无关紧要。在我国资本市场,如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由集中趋于分散将成为常态一样,未来第一大股东性质的转变也将成为常态。国有企业进入什么领域,同时退出什么领域,要依据战略调整方向和业务开展熟悉程度,做到有进有退、有守有为(参见本书“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性质的转变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说前面的讨论更多地涉及我国资本市场进入分散股权时代理论上可以借鉴的控制权安排模式,接下来的讨论则有助于我们认识我国资本市场内在变革的动因。控股股东“一股独大”和控股股东的国有性质被长期认为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权利保护状况的改善和风险分担意识的加强,原第一大股东倾向于选择分散的股权结构。我国国有企业开始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参见本书“理解混合所有制”)。持有优先股的国有资本可以很好地实现保值增值、增进全民福利的目的,而民资则从中看到了国有资本混改的诚意和所做出的制度承诺。对于在混改过程中推出的国企高管限薪和员工持股计划,我们从完善混改实际效果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参见本书“完善治理结构:国企薪酬问题的根本出路”和“国企混改,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样的员工持股方案?”)
除了控制权安排制度的创新方向和混改提供的内在变革动力,分散股权时代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还有赖于公平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而2016年11月在学术界掀起的围绕产业政策的大讨论事实上从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进入分散股权时代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问题。既然进入分散股权时代,无论“野蛮人”的接管威胁,还是管理层反并购条款的实施,都有赖于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由于不仅缺乏制定科学合理产业政策所需要的当地信息,同时缺乏避免制定产业政策扭曲的制度保障,现实中更多的产业政策成为“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张维迎),人为地制造不公平竞争(参见本书“产业政策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和“政府具有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吗?”)。
进入分散股权时代,随着原来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下降、大股东以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减弱和分散股东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在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小股民起义”推翻大股东议案的事件屡见不鲜(参见本书“公司章程修改,股东为什么会投反对票?”)。我们看到,在更换董事会重要成员、公司章程修改等重大问题上,既不应该是部分股东,也不应该是代表部分股东的部分董事,而应该是全体股东用手中“神圣的一票”来做出更符合大多数股东利益的最终裁决。
那么,在进入分散股权时代后,我国上市公司应该如何选择公司治理模式呢?我们认为,首先,未来需要使股东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而使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成为体现股东意志、保护股东权益的基本平台。其次,在内部治理机制设计上,从依靠控股股东逐步转向依靠以利益中性、地位独立的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当管理团队与新入主股东发生冲突时,独董提议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则成为协调双方意见分歧重要的机制。最后,在外部治理机制上,发挥险资、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积极股东角色。
在这次以“险资举牌”为特征的并购潮中,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向那些仍然沉迷于“铁饭碗”的经理人发出警示:虽然原来国资背景的大股东可能并不会让你轻易退位,但新入主的股东则可能使你被迫离职。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已从原来的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转为以“野蛮人入侵”为代表的股东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为了建设和完善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我们需要在借助外部接管威胁警示不作为的经理人和保护创业团队以业务模式创新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实现良好的平衡(参见本书“在分散股权时代如何选择公司治理模式?”和“如何使险资、养老金成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
本书收录了我们对随着分散股权时代来临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模式转换阵痛期的经济观察笔记,全书共由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21世纪商业评论》《财经》《董事会》和FT中文网、财新网等报刊和媒体上的共30篇经济评论组成。在本书出版时,我们将这些文章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为既相互独立又内在关联的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