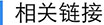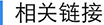|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盒 长6.5cm |
 |
|
清乾隆 珍珠地珐琅彩火镰盒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 高6.5cm |
 |
| 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 吉服带 带长184cm |
 |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孝贤纯皇后绣花卉火镰荷包 长5.2cm |
 |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火镰盒 高 6.5cm |
 |
|
故宫博物院藏 织绣火镰袋 华辰供图 |
满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重视骑射传统与围猎活动。行军在外需带火种,满人便有随身携带火镰、燧石与火绒的习惯。需要取火时,将火绒包裹住燧石,与火镰摩擦,即可生火。入关后,为了不忘记本民族的传统,清王室恢复了古代狩猎阅军的制度,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康熙、乾隆两朝,每年都举行大型的狩猎活动。火镰仍具有实用性,火镰袋、鞘刀、荷包及扳指袋等,成为男性腰带上的标配: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及嘉庆吉服带上,皆拴挂火镰。乾隆皇帝在他的御用旅行文具箱中,也放了火镰,以备出行使用。
火镰常被赏赐给大臣,尤其是战场得胜的将士。康熙五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镇守陕西延绥等地总兵李耀奏谢皇帝所赐“火镰荷包一个……”,皇帝还要李耀“见这火镰荷包,如见联的一般”;嘉庆十年巡幸盛京,入筵宴之随驾百官贝勒、宗室觉罗、蒙古王公、朝鲜使臣等各赏缎匹、小刀、火镰等物;另据《文宗实录》中载,咸丰三年十月,平灭太平天国三战三捷,“各路带兵大员及将弁兵勇、均能用命,深堪嘉尚,著发去金鞘牙柄小刀十把、银鞘牙柄小刀十把……火镰十三把,著胜保择其奋勇出力者,传旨分别赏给”。有记载提到,清代卤簿中宝象驮着的宝瓶中,贮有“火绒、火石、火镰”。可见火镰是“敬天尊祖”的象征。承装火镰的器具可见织锦、瓷制、牙雕等多种质地。因材质不同,而有火镰袋、火镰包、火镰荷包、火镰盒、火镰套等不同称呼。清宫档案中,也有时称其为“燧囊”,其内装火镰、燧石及火绒。乾隆时,孝贤纯皇后听闻丈夫乾隆皇帝谈及祖宗的简朴传统,亲手为乾隆制作了一个火镰荷包,以彰显朴素之风。皇后选择火镰荷包,而不是普通荷包、扳指袋等,或许有偶然性,但也能看出火镰在清宫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所具有的代表性。火镰及其盛装器具成为满族生活的一种象征。
当一件实用器,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精神内涵,便超越了“用”与“器”,成就了从实用器到陈设器的转变。乾隆皇帝会把火镰荷包,连同其他心爱的小文玩,一起放在多宝格或小柜中赏玩陈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可见,紫檀雕云龙纹小柜中,有黄缎彩绣福寿纹火镰荷包一件;紫檀嵌彩瓷博古图小柜中,有银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荷包一件……
火镰盒的承装都颇为讲究。“包装”最隆重的,当属孝贤纯皇后过世前一年为乾隆做的火镰包。乾隆后命人以内有黄绫的织锦将荷包包好,外配金漆盒,之外再配木盒。木盒上刻有乾隆满汉双语诗文及序言,及臣子庄有恭、蒋溥、汪由敦等人之题铭赞赋,彰显着乾隆对皇后的无限怀念。满族人从配挂火镰,到用火镰盒装火镰,再到为火镰盒配盒,将火镰盒变成了艺术品珍藏。
此件瓷胎珍珠地珐琅彩火镰盒分盖与身两部分,两者左右各设一耳,供穿绳,以使盖与身不致脱离。盒身之耳巧做蝙蝠形,施矾红彩,寓意“洪福齐天”。火镰盒内施松石绿釉,外壁以锥拱技法作锦地点纹,并凸饰金花,足内施松石绿釉,中间留白处以矾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横款。形制相仿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乾隆时期制作的,瓷胎洋彩西洋人物山水火镰盒,尺寸稍短(7.5cm),高度相同,底以矾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四面开光,内绘西洋风景人物。开光外同样以锥拱技法,并加饰金花,似在模仿皮革织绣的纹理。另有一火镰盒,尺寸相仿(高6.5cm、宽8.2cm),制作方法与前者极为相近,但纹饰有别,且底书蓝料款,亦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就目前所查到的资料来看,瓷胎上加锥拱技法,应意在模仿金属器或皮革织绣。台北故宫藏清代镀金嵌松石珊瑚火镰盒,其外壁与上述几件瓷制盒皆以细密凸起装饰,风格颇为相似,华美富丽。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火镰袋亦可见相似纹路。此件火镰盒富贵华丽,典雅端庄,工艺繁复,且瓷制较难保存,而尤为难得。瓷质火镰盒的实用性似乎远逊于缎锦、犀角等材质器皿。但它或许是火镰盒从实用器转身为陈设器之最佳注脚,传承着高超的制瓷工艺,浓缩着满人对自己民族传统的回望与继承,凝练着敬天尊祖的精神追寻。